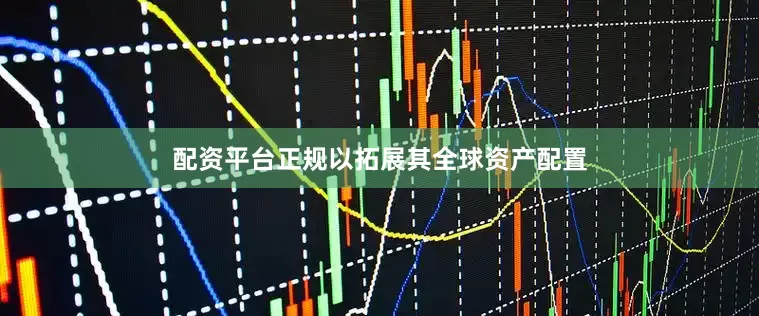日前,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《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(二)》中明确提出:劳动者未知悉、接触保密事项的,竞业限制条款不生效;即使属于涉密人员,竞业限制条款约定的竞业限制范围、地域、期限等内容,应与劳动者知悉、接触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相适应,超过部分无效。
近年来,竞业协议被滥用的情况屡见不鲜。从互联网大厂的普通客服到教育机构的基层讲师,都曾深受其困扰。甚至在今年4月,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第四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里,就出现了月薪三千五的保安,在跳槽后被索要二十万竞业限制违约金的情况。
这导致不少劳动者在压根接触不到核心商业秘密的情况下,被一纸强行签订的竞业协议剥夺了行业再就业的权利,甚至面临“全行业封杀”的困境。而对比企业,普通劳动者维护自己权益的手段更为单一,能获得的社会资源和支持也不足,很可能面临着身心的双重消耗。
法律创设竞业限制制度的初衷,是保护企业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、防止恶性竞争。倘若竞业协议被扭曲为限制人才流动的“软枷锁”,无疑背离了这一初衷。更值得警惕的是,不少企业常以低额补偿金绑定高额违约金,普通员工离职后每月仅获数千元补偿,违约却需赔付数十万元,守约成本与违约代价显然不相匹配。
从长远来讲,这既不利于平衡劳资关系,也违背了人才有序流动的现代人才观。
新司法解释的发布,格外强调竞业限制条款不生效的条件,也进一步划定涉密与否的边界。此前,竞业限制滥用的根源之一,正是“涉密”概念的模糊性与宽泛性。企业常通过一纸保密协议,将普通劳动者转化为“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”,却无视其是否实质接触核心秘密。此次最高法以典型案例释法明义,辨析了是否属于涉密人员的实践情况,显然具有鲜明的启迪和指导意义。
当然,尽管司法解释的出台为“竞业”的判定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,也给出了涉密情况的有力辨析,但在实践中仍可能面临更复杂的情况。毕竟,在生产经营活动中,特别是在各种新经济形态、新产业形态层出不穷的背景下,企业商业秘密的认定并非一目了然。比如,客户名单、供应链数据等商业信息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“秘密”?不同岗位员工接触秘密的深度与广度不同,所承担的竞业义务又该如何划分?若缺乏细化的指引,或将继续出现一轮轮司法博弈。
破解困局的关键,或许在于构建更为精细和更具实操性的认定体系。对企业来说,显然有必要重新梳理自身的保密体系和判断标准,对不同层级员工的管理要求和相应协议应当更加精细合理,不能以“保密”二字“一刀切”;对司法机关来说,更应该兼顾法理依据和实际情况,让竞业限制回归保护创新的初心,而非异化为阻碍流动的藩篱。
说到底,人才流动是市场经济繁荣的基础条件之一。人才的充分涌现和自由流动,离不开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。破除不合理束缚,才能更大程度激活创新源动力,从长久来说,更多企业将受惠于此。
深富策略-深富策略官网-十大正规配资平台-好的股票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